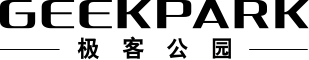跟攀登梅鲁峰比起来,攀登珠穆朗玛峰就是在树林里散步。
在二十世纪喜马拉雅登山运动盛行之前,对当地的尼泊尔人和西藏人来说,攀登高耸的雪山顶峰不是精神失常,就是亵渎神灵。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座雪峰自然是珠穆朗玛峰,作为地球最高点,它吸引了一波波怀抱各种动机的登山者。直到今天,成熟的商业运作让珠峰成了旅游景点类的存在,大部分工作交给向导和脚夫,只要付钱就能站在世界最高点拍照留念。
然而还有另一种攀登,《进入空气稀薄地带》的作者乔恩•克拉考尔 (Jon Krakauer) 将它称为与攀登珠峰完全不同的运动——攀登梅鲁峰 (Meru)。
它在喜马拉雅山脉末端,位于印度北部,高 6400 米。与珠峰不同,你不可能雇佣到愿意去那里的脚夫,因为太陡峭了。峰顶名叫「鲨鱼鳍」,那是它的形状,同时也因为它不可思议地光滑,这让攀登变得几乎不可能。克拉考尔评价,跟攀登梅鲁峰比起来,攀登珠峰就是在树林里散步。
2011 年之前,世界上最好的攀登者试着攀爬它但都失败了,直到三个美国人最终站在上面:Jimmy Chin, Conrad Anker 和 Renan Ozturk。不久前上映的纪录片《攀登梅鲁峰》(Meru)纪录了人类在攀登雪峰这件事上的又一历史性事件。
 (《攀登梅鲁峰》纪录了三个美国攀岩者两次尝试攀登梅鲁峰的经过。它获得了2015年圣丹尼斯电影节观众奖。)
(《攀登梅鲁峰》纪录了三个美国攀岩者两次尝试攀登梅鲁峰的经过。它获得了2015年圣丹尼斯电影节观众奖。)
2008 年他们三个人第一次尝试攀登梅鲁峰,在离峰顶不到 150 米时放弃攀登开始下降。那次攀登刚开始没几天他们就遇到暴风雪,外面气温零下 20 度,几个人缩在帐篷里度日。等到暴风雪过去终于能攀登时,食物和时间双双流逝。最终在距离峰顶 30 米的地方,他们面临一个选择:冒险完成最后一段的攀登,这可能需要 4 到 6 小时,意味着他们需要在 6400 米海拔处过夜,这非常危险,然而目标近在眼前。或者接受失败,打道回府。他们选择回去,那时候已经暴露在严寒中太久,等回到印度发现大家的脚趾头俱已冻死。
这只是故事的开始。当攀登一座山的念头起来后很难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三年后 Conrad Anker 决定第二次尝试,然而这次很多事情发生了。先是 Renan Ozturk 发生滑雪事故,人险些丧命,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才能走动。不久 Jimmy Chin 又在滑雪中遇到雪崩,当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后居然奇迹般生还。还有 Conrad Anker,这位近 50 岁的攀登者很难不顾家人感受将自己置于险地。电影花大量篇幅讲述这三个人的挣扎和考量,拷问着一个老问题:为什么要攀登?为什么要去冒险?
Jimmy Chin 的回答是,在攀登的时候他才是他自己,是一个更好的人。
早已逃离自然、躲在城市里的人类远离大部分真正的危险,与我们的祖先比起来,现代人生活的主题是安全和舒适。攀登雪峰将人重新置于危险之中,一切变得严肃起来,那些冷静、 无畏和信心的人幸存下来,做出了不起的事情。
约翰•穆尔在十九世纪时就意识到这点,在美国镀金时代,他住在荒野中,长久地流连在山间。他写道:自然是我们本真的一部分,是社会试图让我们忘记的自己。回到自然中是重新找回自己的一种方式。去登山就是回家,自然是必需品。
人类向往舒适,于是发明创造无数科技产品让生活越来越舒服。奇怪的是,人类同时又对冒险怀抱着同等渴望。似乎只有冒险才能让我们在被事无巨细照顾着的城市生活中感受到自己活着这个事实。
《心事如山》这部探讨登山历史的书如此解释登山的动机:中产阶级需要一个打开危险的阀门供他们释放在养尊处优的城市中聚集起来的精力。
攀登梅鲁峰不止是释放精力,它的危险让整个过程更扣人心炫,登上它的回报是不可度量的激动,这种激动很多人终其漫长的一生都不会感受到吧。
头图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