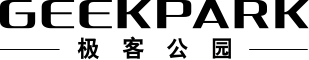中心化的科技巨头早已渗透到了互联网的层层面面,为什么原本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沦落」到如今需要奔走呼号,呼吁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经济学人》这篇文章从互联网诞生时的架构设计结合数字经济学中「网络效应」和「连锁效应」给出了答案;在政治和互联网的关系如此密切的当下,孕育出了 Clicktivism(网络点击行动主义)和克它的 Bot,这二者对政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前不久的 Linux 社区之争,掀开了科技行业长久以来的观念冲突:多样化和能力到底哪个摆在首要位置……这里是 TechBoard 第二十三期。 TechBoard 是一个全球视野下,甄选每周重要科技评论的栏目。我们将以摘要的形式引入值得阅读的科技评论文章,并鼓励读者去阅读原文。
层层而上的互联网故事:从开放到封闭

1999 年,两位经济学家 Carl Shapiro 和 Hal Varian 出版了一本名为《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战略指导》,至今仍被视为是数字经济领域教科书级的出版物。两位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信息定价、注意力、技术生态等放在今天仍在讨论的概念。这本近 20 年前出版的书,其中谈到的经济规律,在当今互联网世界依旧生效,尤其是书中重点提到的「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20 年前让人们理解了微软和 Windows,也给带出 Web2.0 时代的 Google、Facebook 指明了道路,作者之一的 Hal Varian 则在 2002 年成为了谷歌首席经济学家。
《经济学人》这篇文章,不是要老生常谈巨头垄断、日益集权的当下互联网环境,而是想用「网络效应」、「连锁效应」(knock-on effects)和其他经济规律来梳理和分析互联网,为什么原本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沦落」到如今需要奔走呼号,呼吁去中心化的互联网。
如果说要把互联网具象化,可能很多人可最先联想到的是一张靠无数点交织联结起来的大网,但实际上,互联网就像绝大多数的数字系统,它是基于层层而上的「层级(layer)」设计出的。最底层的是得以让我们连接上路由器或者输入 Wi-Fi 密码就可以「上网」的基础设施框架和信息交换的协议,在这个层级,互联网还称得上是去中心化的,尽管现实生活中可供我们选择网络运营商不超过五家,但没有一家公司可以控制信息交换的协议。
然而,除了技术人员,普通网民不会在意甚至都不了解这些基础设施,我们更在意的是上网要做什么,而不是网是怎么联上的。这也就引出了再往上一层,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谈论的互联网,一个已经变得非常中心化的互联网,以及基于第二层延伸出的第三层中心化的互联网。
这里用一个比喻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第一层的互联网就像大地,它支撑着地面上所有的活动。我们通常都身处第二层的互联网中,使用着搜索、社交网络、数据传递等互联网服务。在此之上还笼罩着「大气层」,也就是第三层互联网,它包括如今覆盖率超过 98.2%(2017 年底 netmarketshare 的统计数据)的两大手机系统 iOS 和 Android;亚马逊、谷歌、微软三大公司统领的云业务;Facebook、谷歌、亚马逊手上的数据……
如果说底层设计互联网的初衷是去中心化,只用于传输数据和信息,那怎么到上面层级就变得如此中心化了呢?
最初是互联网先驱们,那些底层设计者在当初过于理想主义了,他们认为当时制定的协议,已经足够防止中心化的倾向,但在协议推出后,互联网的协议机制并没有发挥出想象中的治理作用,被许多开发者有意无意地钻了空子。比如早期互联网上的电商无法获悉顾客之前的购买记录,开发出点燃互联网热潮的 Mosaic 浏览器的网景公司,给出了以缓存(Cookies)形式的解决方案,再后来,这些数据不只是「缓存」在服务器上,而是永久保存。当互联网开始有了「记忆」,网络效应就开始在拥有「记忆」的那边发挥作用。
但当时的互联网,用户需要付网费但还没有为内容付费一说,丰富的网络世界是免费的,对用户而言,难的是聚合以及如何不迷失在互联网里。因此,各大公司的首要任务变成了如何吸引到更多的用户,谷歌在上世纪末超越了曾经全球最知名的搜索引擎 Alta Vista,靠的就是它简洁的界面和快速且准确的搜索对用户有足够吸引力,一旦优势建立起来,服务吸引用户,用户量吸引网站「入驻」,网站多了用户搜索体验就更好……这个循环让谷歌就像踩在了正在下坡的飞轮上,网络效应和连锁效应双重加速度,使得谷歌迅速脱颖而出,在竞争对手反应过来时,早已望尘莫及。同理,基于这种以收集用户数据,贩售给广告商的商业模式得以成功的前提,它们都曾踩在这个飞轮上。
再仔细审视互联网的三个层级,我们会发现,这些中心化的科技巨头早已渗透到了三个层级。比如谷歌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数据中心,该数据中心处理了互联网总流量的四分之一,为了推动云业务,谷歌还在建造太平洋到北海的三条水下光纤电缆……这些投资,也只有这种体量的公司「砸」得出来,它也让竞争对手更难以追赶。它们基于底层互联网,在第二层互联网起家,如今则彻底垄断了第三层互联网,同时它们还可以把三层互联网都调动起来,为未来自己的「飞轮」铺路,比如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语音面部识别……
曾经细微的一个技术变革经过层层堆砌,就像把分散的网格一块块缝起来一样,当我们现在看这「张」互联网时,它已经被缝成了一块块布。如今想再把这块布撕开,只能靠另辟蹊径的技术,来再次颠覆数字经济了。但技术会改变,经济规律却不那么好变,不然,20 年前的一本书,怎么至今仍经久不衰呢。
Bots 如何毁灭网络点击行动主义(Clicktivism)
近两年来,有两个词语被社交网络赋予了新的意义,一个是「老词」Bot,在各式各样的社交媒体 Bot 涌现前,这个词上一次大规模出现还是在 CS 游戏中,它指的是互联网上化身为机器人的程序,而在这两年 Bot 从游戏中走到了社交应用上,从 Twitter、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到 Slack、Telegram 类的通讯软件,都出现了 Bot 的身影,只是作用不同,前者更多是「乔装成人」来发布动态,后者则更像是帮助人们提高效率的软件助手。
另一个则是被创造出的新词:网络点击行动主义(Clicktivism),2016 年的美国大选已经不仅关乎政治了,它还对英语产生了影响,因为这次美国大选中政治和互联网的关系太过密切,光是反应这些「网络政治活动」的各类词语就给牛津在线词典增加了 300 多个新词条,其中就有 Clicktivism,它指的是使用网络作为影响公众对政治、宗教或其他社会问题看法的主要手段的行为或者习惯,包括在网站上发消息、网络请愿、或者群发邮件。这个词略带贬义,即是讽刺那些仿佛在家里动动手指投投票,公共政策就能天上来的不切实际「社会活动家」们,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 Clicktivism 的行列中,或许是因为这既方便,传播力度又大,同样还能给予「参政议政,感觉良好」的自我满足感。

这篇文章标题中提到的 Bot,特指近年来让 Twitter 又爱又恨的各类政治 Bot,它克的就是 Clicktivism。
Clicktivism 起于社交媒体的兴起,当社交媒体兼备了「社交」及「媒体」两种属性后,政治就不可避免的介入其中了
。政客和社会活动家开始利用社交媒体作为政治工具,它不仅传播范围广、成本低,且传播力度更大,比起投放在电视、报纸和网站上的政治广告,来自可信赖的社交关系中传播的新闻更具有实实在在的影响力。同时,不怀好意者也马上参与到这股政治潮流中,除了传播假新闻外,它们还造出了「假人」也就是 Bot。
Twitter 上真假 Bot 难辨已经成为这个平台的一个顽疾。不同于各类兴趣爱好或者互联网meme式的 Bot,政治 Bot 通常不会在自己账户名后加上「XXX Bot」以示身份,正相反,它们巴不得被用户认作是真人。各种组织的官方推特通常都爱说「官话」,因此很容易创造出相应的假分身 Bot,公众真假难辨,而因为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一旦 Bot 带起节奏,它造成的影响也是难以挽回的。就在「Twitter 参政涉政」的最高峰 2016 年美国大选中,真实的社会活动组织和程序假人 Bot 就混杂在一起,真实的用户则沉浸在各种 Clicktivism 的传播中,谁也不知道原推到底是出自人还是 Bot 之手。直到现在,对各类社交媒体平台涉政的调查仍未结束。
随着假新闻假账户的丑闻不断爆出,用户在一次次上当受骗后也提高了自己辨识 Bot 的能力,比如一个账户的推文内容都很相似,还都带有丰富的 #主题 标签以及表情符号,八成这个账户就是 Bot……吗?不,正是因为 Bot 的出现,才让这些「官话」背后的传声筒,变得真假莫辨,平台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如何避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负责处理平台假信息的研究人员曾统计出了一系列标准,试图教给算法如何识别 Bot,其中包括内容、信息扩散者和传播模式。但算法面对一条推文,它在识别的同时也在「吸收」,因此,恶意带算法的节奏也可以实现,就像影分身会让敌人难辨其中的真人,当你的邮箱被大量类似的邮件塞满时,你很难能集中注意力从中辨认出垃圾邮件和有用邮件。
Clicktivism 也往往和「量」绑定在一起,比如投到多少票、转发多少次后就会有什么的回报和进展,而刷量正是 Bot 最擅长的,但分不清转发点赞支持的到底是真人还是 Bot,这不仅会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还会给政客们的政治风向评估带来误解。无论是两年前的美国大选,还是马上到来的 2018 年 11 月中期选举,如何辨识真假新闻和账户,社交媒体们还没有给出满意的方案,而最好的办法还是老办法:靠你自己的判断力。
真实的信息难以传达给需要接受它的真人,虚假的信息被虚假的 Bot 一次次扩散,真假的边界就这么被模糊了。亦真亦假的社交媒体影响着半实半虚的政治,《纽约客》经典的那幅漫画所述「谁知道屏幕背后是人还是狗?」在现如今却间接成了真。
Linux 平台上的文化战争

上个月,Linux 之父 Linus Torvalds 宣布将暂时退出 Linux 社区,休息一段时间,并为他多年来在社区上对 Linux 开发者的抱怨、辱骂等不当行为道歉。
近乎同时,Linux 社区也颁布了新的行为准则(CoC ),核心就是围绕如何塑造个「良好的」 Linux 社区环境,让社区成员免于受到歧视和攻击,但很快这就引起了社区的骚动,一部分开发者开始批评 CoC,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应该根据能力而非信念来做出判断」,并威胁称要撤销部分 Linux 的代码。先不说倘若真的有开发者撤销了 Linux 的代码会对整个互联网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次纷争的起源早已是房间里的大象,它是科技行业的一场观念冲突:多样化和能力到底哪个摆在首要位置。
据《纽约客》的报道,Torvalds 的暴脾气和口出狂言伤害到了许多开发者的「感情」,尽管他骂人用词不分性别,但女性总是在炮火的最前列。据 Linux 基金会和研究人员的估计, Linux 程序员有十分之一为女性,但这十分之一中很少有知名的女性内核开发者。
早在 2015 年,Linux 社区就颁布过一份《冲突规则》的文档,在其中 Linux 基金会表示希望在软件行业看到多样性,Linux 社区欢迎任何人,如果你在社区感觉到不适,可以联系 Linux 基金会,但 Torvalds 本人,就是这份文档行动虚设的证明。而新出台的 Linux 社区行为准则则是要把过去三年内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的《冲突规则》进一步明确化,比如「不许进行基于性别、性取向、种族、信仰……进行各种方式(如图片、言语、人肉)进行歧视和骚扰。」
正是这份「明确」,使得反对 COC 的开发者们非常不满,他们认为 Linux 是基于个人能力判断的一个开发者环境,而非开发者的身份,Linux 诞生的初衷,是为了推动更开放、更多元、更自由的互联网环境。支持修订 COC 的一方则表态称,如果真正的开源是建立在任人为才的基础上,参与者对社区的智力贡献决定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力,那么现在 Linux 甚至整个软件行业都由白人男性主导,是否是在间接表示白人男性比白人女性和少数族裔在智力上更有优势,进而能让他们作出更多的「智力贡献」?这一派通常秉持着「你后天形成的能力是基于你成长的优渥环境,你应该为多元化出一分力,而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而反对多元化。」的观点。从去年 James Damore 在谷歌内部分发的「意识形态回音室」备忘录到如今的 Linux 社区争论,这两类观点一直都是软件行业甚至许多白人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的争论点。
除此之外,出于观念不合,开发人员是否有权利撤销自己贡献的代码也是这次 Linux 社区观念之争引发的另一个软件行业的议题。Linux 基金会技术顾问委员会的开发人员 Jonathan Corbet 认为这种行为不仅不合理也不合法,随意撤销开源项目中的贡献代码,是涉嫌侵犯通用公共许可证(GPL)的违法行为。如果任何开发者都可以随意撤销自己在开源软件项目中贡献的代码,那这份代码既是他的贡献,也可能成为他威胁他人的武器,像 Linux 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大规模使用的软件项目,只是悄悄的撤销代码都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尽管 Linux 社区在之前几轮争议后,已经完善了「防代码撤销机制」,但这不只是 Linux 社区的问题,而是开源伦理的问题。
这场纷争缘起于对多元化的观念之争,Torvalds 在 CoC 发出后出面回应,他称他不歧视任何人,他骂得是糟糕的代码和为写出糟糕代码找借口的人。是否能写出好的代码和是否要推动多元化并无冲突,正如「开源」这个定义及开源运动发起人之一的 Bruce Perens 所说,我们需要多样性,但对真正好的作品进行评价时是不需要带着意识形态视角的,开源社区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伟大的事。
延伸阅读与参考:
「Master」「Slave」等代号从 Python 语言中移除
摩尔定律的终结
1965 年,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了摩尔定律,既每 18 - 24 个月,同样的价格买到的集成电路,上面容纳的元器件数目和它的性能会增加一倍,这种趋势自该定律被踢出后已经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上世纪六十年代诞生的世界上第一批集成电路只有 10 个晶体管,今天最复杂的硅芯片则有 100 亿个晶体管,正如同十年前发布的第一代 iPhone 的 320x480 的分辨率已经不如刚发布的 42mm Apple Watch 4 的 384×480,无论是支撑技术革新还是缓慢迭代,摩尔定律总结的趋势一直延续至今,且异常准确。

可摩尔定律终归只是一个观测和基于归纳法的「预言」,它并不是一个定律,无论是物理学家还是摩尔本人,都认为摩尔定律将在 2020 年左右失效。《硅谷秘史》的作者,精益创业之父 Steve Blank 近日撰文指出,摩尔定律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失效了,只是消费者还未察觉。
摩尔定律的提出是基于对加工过程技术和经济学的观察,加工过程随着科技进步效率和成果都越来越好,但终归无法突破物理定律,晶体管再小,功率密度也是保持不变的,它遇到的临界点被称之为「功率墙」(Power Wall),自 2005 年起,微处理器的频率就被限制到了 4GHz 左右。各家芯片大厂都在努力突破这堵功率墙,它能否被打破还说不准,但螺旋式上升的制造成本、芯片厂商之间的技术壁垒、收益递减的风险……这都使得基于「硅」的芯片或许不再是未来的创新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息技术前进的步伐就会就此放缓,反而这是进入下一个新篇章的前奏。
Steve Blank 认为新篇章不是聚焦在「我们能把芯片研发的有多好」,而是「我们能用这么好的芯片做什么?」,就像每年更新换代,性能都「大幅提升」的手机,厂商所言的超频、跑分、新工艺是否真正被消费者、开发者和设计师所充分利用,换言之,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性能过剩」而非「压榨性能」。正如人类大脑中 1000 亿个神经元的数量在过去的三四万年内都没有变,但我们在过去三四万年内开创出了可以让我们知道大脑中有 1000 亿个神经元的文明。在芯片领域也应该如此,如何充分利用好 100 亿个晶体管的硅芯片才是未来创新的方向。
在芯片上安装晶体管数量每两年翻番的定律已经结束,但新的计算机架构、芯片封装技术、低功耗内存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未来几年内马上到来的 5G 也将把许多储存需求转移到云端,硬件创新也并未暂停,AR、VR、显示、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等领域还远未到能配得上 100 亿个晶体管芯片的地步。最重要的方向之一,还有乔布斯曾经所言的「硬件是软件的载体」,每个人脑中都有 1000 亿个神经元,想想能用它做什么或许比试图让它数量增加来得更有意义,更何况是卡在物理定律上的芯片呢。
编辑:宋德胜
题图:Raj Verma